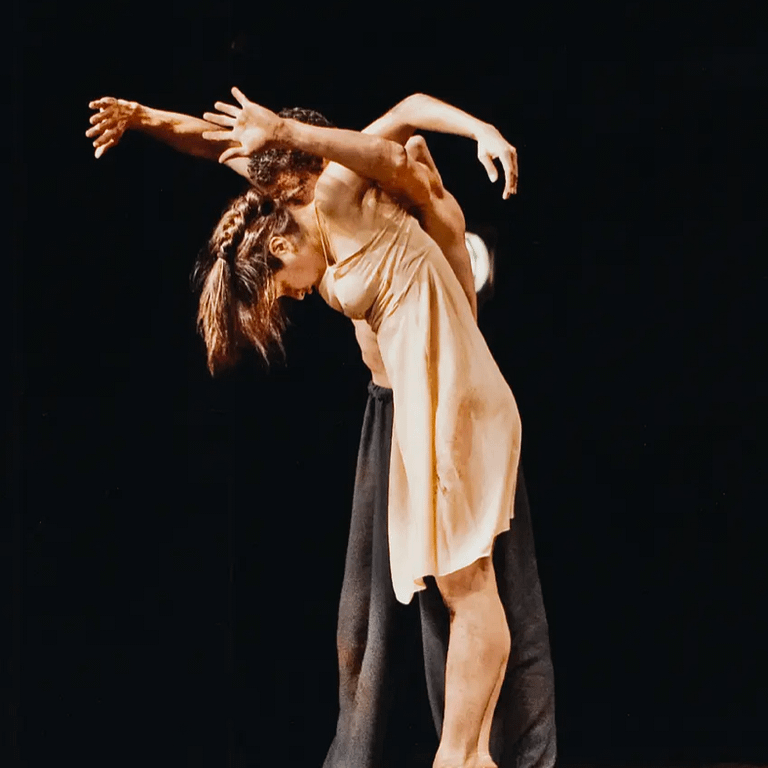自從舞蹈家碧娜・鮑許的紀錄片《Pina》於 2011 年上映之後,越來越多人對這位來自德國的舞蹈大師充滿好奇,她不僅打破了舞蹈和戲劇之間的界限,更將人物個性與個人情感融入作品之中,打造了如《七宗罪》、《春之祭》等無數佳作,而她多樣性的創作思維其實與從小的生活環境以及遠赴重洋的學習經歷有關。
碧娜・鮑許——以「舞蹈」貫穿生命
「當我回顧我的童年,我的求學階段,以及我開始編舞的時候,那些經歷是充滿聲音的,也充滿色彩,他們在我的腦海中重複出現,呼之欲出⋯⋯後來,我把這些回憶編寫進我的舞蹈作品之中。」——碧娜・鮑許
1940 出生於德國索林根的碧娜・鮑許(Philippine Bausch)小名 Pina,她的父母在索林根經營一間附屬於酒店的小餐廳。從小開始的餐廳打雜生活也使 Pina 練就了一身察言觀色的能力,來來往往的人群、刀叉碗盤敲擊碰撞,以及到後來二戰爆發,人們恐慌的交談聲、縈繞耳邊的警鈴聲⋯⋯,這些日常聲音和經歷最終都濃縮成為了 Pina 創作舞台劇場靈感來源。

(圖/Pina Bausch Foundation©Ulli Weiss)
分享本圖Pina 十四歲那年開始跟著戰後德國現代舞倡導者庫爾特・喬斯在福爾克旺(Folkwang)學校學習舞蹈,庫爾特嘗試將戰後革命精神融入傳統芭蕾舞之中,並試圖掙脫舞蹈中的芭蕾桎梏,此舉不僅奠定 Pina 能夠自由創作表達技巧的舞蹈基礎,更使 Pina 大量地吸收歌劇、雕塑、繪畫、攝影、設計等多種知識,後也反映在她的舞蹈編導之中。
1958 年,Pina 獲得了 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的資助,遠赴紐約茱莉雅音樂學院習舞。「去紐約留學可以說是一個轉折。」Pina 曾說:「剛開始因為看不懂英文所以充滿挫折,我就連點菜都只能用比的。」然而語言不通並沒有影響 Pina 對紐約的著迷,美式文化影響她深刻,Pina 師從安東尼・圖德、何塞・利蒙等人,同時為自己找一份在大都會歌劇院裡的工作,兩年的歌劇薰陶也使 Pina 的作品中保有對歌劇的親和力與傳統音樂的尊重;兩年後,Pina 重回德國接手福克爾旺(Folkwang)舞團,隨後改名 Folkwang Tanzstudio。
舞蹈劇場 Tanztheater——以「舞蹈」,演繹解放於常規的精神
「我並沒有因為能更加入福克爾旺舞團而滿足,我非常渴望跳舞,更希望在舞蹈之中展現自己,所以我開始了編舞工作。」此時適逢 Folkwang Tanzstudio 需要新作品, Pina 便開始為舞團編寫舞蹈,其後她創造了一系列作品如《Aktionen für Tänzer》等,並在伍柏塔爾劇院院長的邀請下於 1973 年成為伍柏塔爾芭蕾舞團團長,後 Pina 將其更名為伍柏塔爾舞蹈劇場(Tanztheater Wuppertal)。
舞蹈劇場(Tanztheater )一詞來自於魯道夫・馮・拉班,是一種意象的表現手法,更代表著從芭蕾常規中解放的舞蹈精神,使解放後的舞蹈能夠自由地選擇表現方式,Pina 以此精神為基礎,接連開發出了不同舞蹈流派,並以兩部歌劇《陶里斯的伊菲吉妮》(Iphigenie auf Tauris, 1974)和《奥菲斯與歐律狄克》(Orpheus und Eurydice, 1975)展現。
Pina 後來也進行了舞蹈的更多嘗試,像是在舞蹈之中加入流行音樂的《我會讓你進去》(I'll Do You In...)、加入德國古老民歌的《與我共舞》(Come Dance with Me)等。
「《與我共舞》(Come Dance with Me)使用了一首優美的古老民歌,且只有一把琵琶伴奏,沒有合唱團,也沒有管弦樂團。」Pina 的作品總能不落巢臼,而 1975 年她為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的《春之祭》(Le Sacre du printemps)編排的舞蹈更是獲得了廣大的迴響。

《春之祭》(Frühlingsopfer)中被獻祭的紅衣女子,狂舞致死等充滿暴力、恐懼的橋段令人印象深刻,而其中的情感力量和無重力般的身體舞蹈,也使《春之祭》成為 Pina 編舞的里程碑。(圖/Uwe Stratmann )
分享本圖
《七宗罪》(Die sieben Todsünden )結合了舞蹈、歌曲、啞劇、演講,創造出一種全新型態的藝術形式,其中還帶有日常幽默,且保留了《七宗罪》原著裡社會批判的寓意和力量(圖/Pina Bausch Foundation©Oliver Look)
分享本圖四個舞者、五個演員、一個歌手——創造獨樹一幟的 Pina 風格
1978 年,因 Pina 作品中少見傳統舞蹈,所以越來越多表演者不再願意與 Pina 合作。
「許多人認為我的作品四不像,他們因為我年輕,經驗不多所以不認同我⋯⋯舞蹈家們會因為我的成功而驕傲,但更多的是批評我的編舞,有時候我花了很多時間終於想到一些動作,他們卻對我的想法嗤之以鼻,甚至是不願意配合。」在個人回憶錄中,Pina 曾說。
最後她只剩下四個舞者、五個演員、一個歌手,在這樣單薄的陣容之下,Pina 無法排舞,只能改變固有的表演形式,轉以「向舞者提出問題,並用動作來回答」的特殊形式,舞蹈劇最後在同年四月於德國波鴻(Bochum)首演,名為 “He Takes Her By The Hand And Leads Her Into The Castle, The Others Follow”,此劇一出雖因過多性暗示與劇情難解而遭大眾反彈,但 Pina 從這部劇中,也終於找到了屬於她的作品風格。

“He Takes Her By The Hand And Leads Her Into The Castle, The Others Follow” 故事從莎士比亞的悲劇《馬克白》汲取靈感,而標題暗指第一幕第六場的結尾(圖/Uwe Stratmann)
分享本圖Pina 以人們的基本情感為出發點,將人的恐懼、欲望與願望付諸於夢幻、詩意般的圖像和身體語言,引發了一場國際舞蹈的革命,她對現實進行細膩的觀察,將日常生活融入舞台,劇本中的男人和女人坦誠相待,在虛構的故事中打滾生存,致力於尋找幸福。
賦予舞蹈藝術之外的意義
「從事舞團工作最美妙的事情莫過於旅居多國,欣賞世界各地的人文風情,起先是羅馬劇場提出的一個劇場合作案,自此我們逐漸開始著手國際項目。」。Pina 率領團隊以歐洲為起點,與多國如義大利合作《O Dido》、維也納的《Ein Trauerspiel》、洛杉磯的《Nur Du》、香港的《Der Fensterputzer》、巴西的《Água》、伊斯坦堡的《Nefés》、東京的《Ten Chi》等。
2009 年 Pina 與智利合作上演的新作一度引起爭議,最終卻發展成了一個世界性劇場,邀請觀眾與舞者一起參與其中,作品不僅可以納入不同的文化色彩,也對個人與文化給予尊重,甚至成為了文化間的調解人,致力於瓦解任何意識形態,盡可能以最少的偏見看待世界。
在 Pina 六十九年人生旅途中,她指導、設計了超過四十部舞蹈劇場,更打破諸多舊有的舞蹈限制,角色可以唱歌、跳舞,表情可以哭也可以笑,不僅讓看似遙不可及的舞蹈藝術更加靠近日常,同時也為後世舞蹈家開啟了表演藝術的新可能。
參考資料:
- 《PINA》:What Moves me、Talking about people through dance——The life story of Pina Bausch、It did not stop,my dancing
責任編輯/鄧羽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