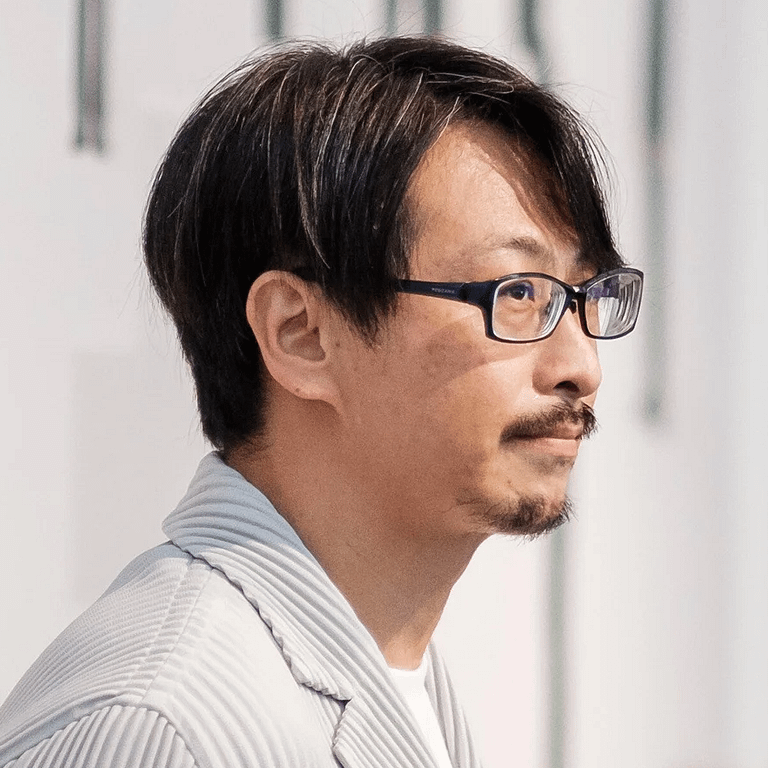從權力的光線到藝術的陰影,林育良始終站在距離的邊界上觀察真實。他曾任蔡英文總統攝影官的攝影師,十年間以鏡頭見證政治現場,也在影像中不斷追問「觀看」的意義。對他而言,攝影不只是紀錄,更是一種語言的試驗——如何在被權力定義的畫面裡,保留藝術的自由與誠實。
從〈The President〉到〈表裡之城〉與〈FUJI〉,林育良用冷靜而精準的構圖解構崇高,讓光線說話,也讓觀者反思自身的位置。這一次,當這些影像走進日本展覽現場,林育良重新定義了攝影:那是一種在距離與親近之間持續對焦的信仰。
在蔡英文面前舉起相機的那一刻,林育良總是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拍的不是新聞,也不是宣傳,而是一種現場的形狀:那個形狀裡有權力的光、有舞台的節奏,也有他對「真實」的懷疑。攝影於他而言,不僅是紀實的工作,更是一場持續的藝術實驗——在權力最集中的地方,思考觀看的邊界。
他長年在國家最高層級的現場拍攝,見過最嚴謹的儀式與最自然的瞬間。對多數人而言,這些畫面是歷史的見證,但對林育良而言,卻是影像語言的試煉;我總覺得,他試圖在權力的場域裡學會控制距離,讓光線與構圖自行說話,並在退一步的空間裡,尋找一種誠實的敘事。

林育良(左)與書法家何景窗(右)合作,從四國琴平開始,延伸至東京 SHIBAURA HOUSE,並將在明年春天進入京都國際攝影節,展出的主題圍繞他過去八年拍攝的「總統影像」,並透過書法文字,與影像進行再次對話。(圖/林育良提供)
分享本圖十年後,他從〈The President〉到〈表裡之城〉、〈FUJI〉,一路延伸出屬於自己的觀看體系。那是一種將紀實推向藝術邊界的攝影方法:既冷靜又情感豐富,既有紀錄的忠誠,也有創作的自由。這次,林育良從四國琴平出發、延伸至東京SHIBAURA HOUSE 的日本展覽,是他對這段歷程的回首及重新梳理,當政治影像被重新編譯成文化語言,當現實回到形式與光的本質,林育良在距離與親近之間,似乎是完成了他心中的構圖。
觀看的學習
林育良從不以「藝術家」自居。他的影像經驗始於商業與紀實的交界,在拍攝企業形象與媒體專題的日子裡,他磨出一種對空間與氣氛的敏銳。那是他在進入總統府之前的訓練—學會在秩序中觀察偶然,學會在光線裡尋找節奏。
真正的轉折出現在 2011 年。他第一次拍攝蔡英文的影像時,還不認識這位政治人物,只是被一種新的影像可能吸引:「我那時候在想,歐巴馬的攝影師可以拍出那樣的形象,為什麼我們不能?」那是一個從「宣傳」起點出發,卻逐漸走向「藝術」的契機。
進入總統府後,他開始重新思考攝影的意義。那裡的每一次快門,都牽涉公眾形象與歷史記錄,但他更在乎的是光線之下的情緒,為了不被框架侷限,他選擇從場域與建築與人物的「對話」進行切入,讓國家場域轉化為他的「劇場」:走廊的陰影、會議室的對稱、旗幟與風的角度,都被他視為構圖的一部分。
他告訴我,自己拍的從來不只是人物,而是那個人物與空間的關係。那也是為什麼,在他的照片裡,蔡英文常以背影出現—透過她的肩膀,觀者得以看見她眼前的世界,也看見一種更真實的距離。在總統府的八年,是林育良攝影語言成熟的八年進程。那是一個必須克制的職場:紀實要準確、宣傳要得體,任何多餘的情緒都可能改變影像的意義,但正是這種壓力,讓他發展出極為精準的美學。

總統府八年,林育良開始思考如何讓這個「舞台」的結構成為影像本身,他也在自身的紀實中加入創作的語法,讓每一次拍攝都同時是紀錄與詮釋。(圖/林育良提供)
分享本圖他說,那段時間像是「在一個巨大的劇場裡排練」。鏡頭前的總統,是角色;背後的紅毯與鏡頭群,則構成舞台的佈景,這時,林育良開始思考如何讓這個舞台的結構成為影像本身,他也在自身的紀實中加入創作的語法,讓每一次拍攝都同時是紀錄與詮釋。
這樣的思考延伸成他後來的個展〈The President〉。那不是一系列的官方肖像,而是一組關於「權力如何被觀看」的作品:畫面中的總統被拉遠、被遮掩、被融入建築或風景之中,你可以說這樣冷靜的構圖裡,帶著他對權力的距離感,也藏著他對觀看的懷疑,「我不是要拍出一個偉大的人,而是要讓觀者意識到自己在觀看一個現場。」
在城市與山之間
跳脫「公職」的林育良,作品變得更靜、更抽象,也更個人。像是〈表裡之城〉,拍的是城市的倒影——玻璃帷幕裡的另一座城市,反射與真實無法分辨,他說,這是對「權力空間」的延伸觀察:那些建築、那些鏡面,和政治現場一樣,都在展示與隱藏之間反覆;〈FUJI〉則更為內省,他沒有拍富士山的壯麗,而拍它成為符號的呈現,當然,這也是也是一個空白:「我想拍的是崇高的另一面,」他告訴我:「當一個象徵太清晰的時候,反而要去看它的模糊。」這種觀看方式,也讓他的攝影從紀實走向哲學層面: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尋找真實。
2025 年秋天,林育良帶著新作前往日本展出。這次展覽從四國琴平開始,延伸至東京 SHIBAURA HOUSE,並將在明年春天進入京都國際攝影節,展出的主題圍繞他過去八年拍攝的「總統影像」,並與書法家何景窗合作,透過文字,與影像進行再次對話。
何景窗的書法筆觸溫潤、帶有流動感,與林育良的攝影形成對位。兩人當初以「辣台妹」為起點,將政治標語轉化為文化語言,讓影像重新回到觀看本身:「在日本展出的好處,是觀者不會先以政治去閱讀,而能從形式與情感切入。」林育良說,展覽的形式也延續他一貫的「開放式劇場」概念。琴平的車站、酒廠與寺院都被轉化為展示場域,觀者在行走中經驗作品;東京 SHIBAURA HOUSE 的透明建築,則象徵他在創作上追求的「通透」。在不同空間之間,攝影從紀錄變成了事件,觀眾的移動本身也成為展覽的一部分。
關於真實與距離
談到攝影的未來,他不急著定義自己:「我從不覺得攝影必須是某一種樣子,它可以是工作的工具,也可以是思考的媒介。」即使在 AI 與影像生成技術蔓延的時代,林育良似乎仍相信「真實」不是在照片裡,而是在創作者與被攝者之間的關係裡。

觀景窗外,林育良似乎仍相信「真實」不是在照片裡,而是在創作者與被攝者之間的關係裡,於是乎,畫面就開始有了故事性與意義。(圖/林育良提供)
分享本圖「影像從來就不是純粹的真實。從我們決定構圖的那一刻,它就被選擇了。」他語氣平淡,卻有種堅定。那也是他十年拍攝生涯中最大的收穫——理解距離的必要。
對林育良而言,攝影不是為了靠近,而是為了讓我們看見靠近的方式。當他在蔡英文面前舉起相機的那一刻,真正被定格的,其實是他對「觀看」的信仰。那種信仰,讓他能在權力的光線裡,看見藝術的陰影,也讓他在光與距離之間,找到最屬於自己的真實。